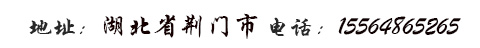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书法中捉对厮杀
|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将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马哈唯物主义结合而来。然而,若论辩证法的源头则首倡中国,如老子的那句名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书法作为一门国粹,其理论及创作也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上。比如清人刘熙载的书论“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不求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就可谓是书法领域中把辩证法运用的很好的一句名言。概因刻意求工,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写出来不尽人意,等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可以达到“无为”之境,返璞归真,“浩然听笔之所之”了。以辩证法的眼光来看,书法中还存在着许多相反相承的理念,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于这六个方面。第一,“顺”与“逆”。毛笔在运笔过程中有“顺锋”、“逆锋”之分。笔锋运行方向和笔杆的倾斜方向一致为“顺”,反之为“逆”。“顺锋”之力为“拖”,造成的线条光洁流畅;“逆锋”之力为“推”,造成的线条多干涩挺拔。“顺而无逆则滑”,形成的线条就会缺乏骨力,有浮滑之弊;“逆而无顺则滞”,形成的线条会瘦拙干涩。此即梁武帝所说“纯骨无媚,纯肉无力”。第二,“提”与“按”。“提”与“按”是使毛笔在空间运动的基本方法。笔“提”线条细,笔按线条粗。有了提按之间的衔接转化,点画才能更有层次感。“提而无按则飘”,点画滑而无力,书法家黄简说“下笔不用力,不能力透纸背,这是‘飘’”;“按而无提则钝”,写出的线条就会粗而无力,成为“墨猪”。刘熙载说:“用笔重处,正须飞提,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坠、飘二病。”第三,“软”与“硬”。毛笔的笔头是“软”的锥体,但高明的书法家却能将其使出“硬”的感觉,此即“锥画沙”及“印印泥”等机锋之意。学会控笔用软,恰当地使力,顶纸而行,化软为硬,先能把“软锥子”当鞭使,再能将其当棍使,一直到“软中有硬”,能使出“金刚杵”般的感觉,方得书法三昧。潘天寿先生说:“用笔忌浮滑。浮乃飘忽不遒,滑乃柔弱无力,须笔端有金刚杵乃佳。”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第四,“方”与“圆”。书法用笔,内擫(点画呈现一种向内按压的态势,擫即“按”)成方,外拓(向上托,向外推,“拓”指“手承物,手推物”)为圆。欧阳询的字多内擫,“背”势用笔,方型收紧,棱角分明,看着清瘦劲健,风骨凛然,颇有阳刚之气;颜真卿的书法多“外拓”,“向”势用笔,字体偏圆,看起来显得雄浑宽厚。王羲之的书法,或方或圆,随意挥洒,其来如风,其止如雨,莫测端倪。王羲之书法第五,“动”与“静”。书法作品是静态的,然而蕴藏的笔势却是动态的。“笔势”者,力之所趋也,是书法中笔力的动态趋向,有人称其为“动态的静态展现”。静而无力则呆,字体徒具其形,缺乏骨力神采,所谓“求形似必堕‘画字’”;动中无静则乱,字体会缺乏从容潇洒的气度。《晋书·王羲之传》称“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可谓抓住了王字美学价值中所蕴藏“动静”之美。第六,“曲”与“直”。书法中的线条有“曲”有“直”,楷书多直,行草多曲,书法家黄简说:“这世界的基本线条只有两种,直线和弧线“。直而无曲则板,直线不能“直中有曲”,就会显得“死板”;曲而不直则弱,曲线如果无有挺直之势,如像弹簧压缩过分而失弹性。“曲”“直”互补,将楷书与草书技法融为一体,方圆兼施,方动静相宜,尽得其妙。此姜夔所说:“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当然,除了这六组主要矛盾之外,书法还存在着大量其它矛盾。如“骨肉”“松紧”“疾涩”“美丑”“刚柔”等,它们如珍珠一般串成中国书法的辩证法项链,既是矛盾的,又是一体的。虽然理论上解释相对简单,但是实际操作中却很多难度,需要高明的控笔能力,加强技法上的修炼。“一阴一阳谓之道”,高明的书法家恰恰就是制造矛盾,并使之成为一体的辩证法高手。他们作书,恰似在玩一种“捉对厮杀”的游戏。无论是逆是顺,是疾是涩,都是将矛盾的双方完美统一起来,并且在这种统一中更张扬了彼此的特点。于是,汉字线条在这种矛盾张扬中就被激活,成为有生命、有血肉的载体。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ozhidingwei.com/zzgxzy/15040.html
- 上一篇文章: 不同产地的珍珠特征,你知道吗
- 下一篇文章: 一周碟讯米希亚最新两张实体专辑正式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