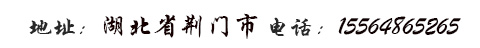李敖憋足劲要和鲁迅一较高下,但单此几个行
|
李敖是很自傲的人,睥睨宇内,目空一切。 某次上电视做节目,主持人小心翼翼地问:“大师会崇拜什么人?” 大师不假思索地说:“我会照镜子。” 实际上,类似自恋、自傲的话,在大师的作品里,是俯拾可见的。 比如说:“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是李敖第二。”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排位。” “新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了,就是李敖,他创造了《虚拟的十七岁》。” “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 “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生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 “古人有大志者‘推倒一世豪杰’,但我认为他们说大话,真正做到此气魄的,乃是千山独行的李敖自己、千古一人的李敖而已。” …… 如此肉麻地吹捧自己,李敖也有非常狡黠的解释:“我一生朋友不多,也不花时间招朋引类,所以‘自大其身’,全靠自己吹捧自己。吃不消我自吹自擂的人应该惭愧,你们本该替我吹的,但你们闪躲,我就只好自己来了。我吹牛,因为你沉默。” 当然,就算是自吹自擂,李敖自己也得有资本,不然,会被人笑的。 李敖有资本吗? 有,写过很多书,很多很多的书。 但李敖自己明白,无论写多少书,要真正成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他眼前有一座大山,必须翻越过去。 这座大山的名字,就叫鲁迅。 为此,李敖就在各种公开场合,还有自己的书里,不厌其烦地评价鲁迅,说鲁迅的白话表述是狗屁不通的东西。 他说:“我李敖讲这种话没有乱说,我现在活得超过鲁迅了,我七十岁了,鲁迅都没有活过六十,今天我写的书量也超过鲁迅了,我写了一千五百万字。”“鲁迅的文章写的并不好,为什么不好?大家看,这是清朝人,看到没有,这些妇女往下看,看脚,缠着小脚,这小脚穿着鞋,脱了以后这个脚就变成畸形到这个样子啊,好可怜啊。胡适和鲁迅他们都承认一点,就是他们是学文言文出身的,所以他们这些学文言文的人出来写白话文,就好像这小脚放大,就不再裹它了,那个鞋也塞点棉花,好像穿的是正常的鞋一样,可是基本上她有小脚的那个结构,那个白话文写起来搞不好就被文言文掐住了,鲁迅的白话文很明显地被文言文卡得很紧。所以我说他的白话文写得不好。第二个原因他受了日文的影响,日文的结构啊啰啰嗦嗦。鲁迅一方面受了文言文的影响,脱胎换骨,小脚放大没放好,一方面受了日文的影响,所以他双重的影响使鲁迅的文字其实写的不好。” 李敖还在自己的评论类节目《李敖有话说》中举例抨击鲁迅的白话句式,说:“……请问这个是中文吗?这个是口语吗?这个是白话吗?请问这是什么文章啊?这叫什么文章啊?你们肯定鲁迅的人,捧鲁迅的人,学习鲁迅的人,赞美鲁迅的人,给鲁迅鼓掌的人,请问你怎么样解释这种句子?有话不好好说,这算什么文章?人们怎么接受这是文学家的话嘛!一个中学生小学生写的这个文章,老师会通过吗?大家再看鲁迅的文章——‘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请问这是什么话啊?” 就因为鲁迅用“营营”一词来表达苍蝇发出声音,李敖非常不屑,说:“这是什么中文啊?你告诉我什么中文?用营营来描写苍蝇,苍蝇用营营来描写吗?大家看《红楼梦》好了,《红楼梦》里面,看到没有,薛蟠,薛蟠最后两个苍蝇嗡嗡嗡,为什么不用嗡嗡嗡叫描写苍蝇呢,为什么用营营来描写苍蝇呢?《红楼梦》这个例子摆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呢?” 其实,鲁迅之所以在此处用“营营”不用“嗡嗡”,是因为在创作这篇《战士和苍蝇》时,他刚与兄弟周作人闹掰,而周作人写了一篇名为《苍蝇》的文章,以苍蝇自比,意欲表现与鲁迅决裂,文末就引用了《诗经》的小雅中这句“营营青蝇,止于樊”。周作人洋洋自得地写: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也似乎没有什么反感。《诗经》里说:“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所以,鲁迅就顺手牵羊,写了个《战士和苍蝇》,还用了“营营”作为苍蝇叫声的形声词,算是刺了周作人一下。 在完成《战士和苍蝇》之后不久,鲁迅还写了一篇《夏三虫》中,里面是用“嗡嗡”来形容苍蝇的叫声的。 平心而论,李敖说鲁迅的白话文因为是“文言文转过来”,并且“受日本语法的影响”,应该是准确的。 鲁迅的文章,今天的读者读来非常拗口也是事实。 但能够因此全盘否定鲁迅在文学史、白话文上的贡献和地位吗? 难道,我们在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白话文小说就没有这种拗口感吗?能因此认为它们是“坏文章”、“不好的作品”吗? 除了狂喷鲁迅,李敖还大贬特贬余光中。 余光中只是慨叹了一句:“私德有如内衣,脏不脏自己知道。声名有如外套,美不美他人评定。” 李敖的才华和作品能否和鲁迅作品相提并论,这里不作评论,单说李敖为了抬高自己,就竭力贬低别人的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 作为杂文大家的鲁迅,一生独力斗群氓,仇敌是少不了的。 但是,斗争归斗争,鲁迅从没有在斗争中通过损人来抬己。 并且,鲁迅从来不对任何人、任何作品的高低优劣做过品评。 单这一条论,李敖已输得一败涂地了。 再说两则小故事,一则关于鲁迅,一则关于李敖。 关于鲁迅的一则是: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研究,耳闻了鲁迅的文名,跟刘半农商议,准备推举鲁迅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逐。刘半农举双手双脚赞成,和台静农商议,让台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的答复直截了当,说:“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当时的中国各方面落后于西方,如果中国人可以摘取文学桂冠,势必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但鲁迅为什么“不愿意如此”呢? 鲁迅说:“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读鲁迅这封信,想起一句老话:只有登顶世界之颠,方知天外有天;因为知道学海无涯,所以虚怀若谷。 那些目空四海,认为天下老子第一,其实往往是井底之蛙。 关于李敖的另一则是:李敖蔑视鲁迅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说鲁迅都不够格称“文学家”。他倒是写了好多本,但大概没什么人记得写的都是什么。就我而言,所想得起,就是一本《北京法源寺》。 为什么特别记得这一本呢?因为,李敖曾想凭借这本小说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专门找来读了。 此书从头到尾都是板起面孔在说教,让人难以卒读。 不出我的意料,李敖连参评的门都没摸着。 事后,李敖不服,愤愤不平、指天划地说:“在历史上,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历来不给中国人文学奖,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但是,莫言后来获奖了。 李敖只好装作什么都没说过。 李敖在生命最后的那段时光,曾借助媒体大发英雄帖,说要与家人、朋友、仇人见上一面,“及此之后,再无相见”。 为什么要见上一面? 李敖说,希望这最后一面是“真诚的,坦白的”,“我会对你说实话;我也想你能对我说真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又相杀”,“我想通过影片,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 原来还是想作秀,顾惜身后名声,想让自己走得不留遗憾,并且,带上点轰轰烈烈的性质。 相较鲁迅,鲁迅却嘱咐家人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情。”“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别人应许给你的事,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靠近。” 对于曾经的怨敌,鲁迅的态度很坚决:“曾想到欧洲人临死前,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人品和格调,高下立判。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死了,很多朋友都为出版他的文集奔忙,其中的许寿裳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做这件事。 李敖的文集,却只能是在他生前早早张罗发行了。 有人这样说鲁迅是“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说这句话的人是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 还有人称赞鲁迅是“鲁迅是二十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说这句话的人是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 当然了,也有人说李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 但说这句话的人就是李敖自己。 也许,再过三十年、四十年,人们应该在鲁迅文章里苍蝇的鸣叫声“营营”“嗡嗡”里会谈论到李敖吧?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ozhidingwei.com/zzgxzy/14045.html
- 上一篇文章: 杭州姑娘晒出5年前购买记录,暴涨一倍这
- 下一篇文章: 朱元璋饥饿晕倒,老婆婆珍珠翡翠白玉汤